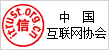一、一個家庭農場的興衰
老劉當過村干部,又是村里公認的致富能手,正值《鄉村愛情故事》熱播,村民送其雅號劉能。
2011年我當鄉長的時候,劉能40出頭,年富力強,流轉經營著三百多畝耕地,是遠近聞名的種糧大戶。
村里人都說他比猴子還精,而前任鄉長則用10個字評價劉能:“既吃苦耐勞,又長袖善舞”。劉能不僅和縣農委的技術骨干都是朋友,就連省城的農業專家,他也結識了不少。2011年,在他的田里,就有和省農科院合作試種的谷子,和農大合作試種的玉米新品種。
上任不到一周,我就登門拜訪了劉能。他家的院子,1畝見方,擺放著各種新式農機具,鐵絲網攏著的玉米棒子堆積如山,墻角下,過道邊,灌溉噴頭、水管隨處可見。
雖然和泥土打交道,但是劉能西裝革履,臉刮得干干凈凈。寒暄過后,他從雪白的襯衫口袋里抽出一支芙蓉王香煙,敬給了我,自己也拿出一支,但沒有點燃,而是隨手擱在了耳朵上。
“今天張教授要來看谷子長勢,下一周李主任也要過來……”
劉能樂觀自信,出口成章。談起玉米、谷子、土豆各個新品種的生長習性,如數家珍,論述起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頭頭是道。他告訴我:肥也不能亂施,必須得通過測土配方,定向施肥才行。
第一次交流,他就令我肅然起敬。縣農委主任評價他為農業土專家,恰如其分。我相信,在劉能的帶動下,全鄉實現農業現代化目標指日可待。
為了進一步鼓勵劉能發揮科學種田的帶頭示范作用,在已經配置了噴灌設備的基礎上,鄉里又爭取上級投資,在一塊集中連片的200畝耕地上,為劉能免費提供了當時國內最先進的膜下滴灌設施。由于本省企業不能提供相關技術支持,最后還是聘請了新疆石河子市的技術人員前來安裝、指導、培訓。
劉能躊躇滿志,鄉里也對其寄予厚望。從2011年到2013年,劉能順風順水,由種糧大戶發展為家庭農場,并牽頭成立了農業種植專業合作社。
許多村民外出務工、經商,村里的承包地讓親戚朋友耕種,地租給多少算多少,一般超不過200元每畝。劉能集中流轉耕地,出300元流轉金,這在當時就是財神爺才能給的天價了。
普通家庭畝產1000斤玉米,劉能通過科學種田,畝產可超過1500斤,多出來的產值遠遠超過了流轉費用!種3、4百畝玉米,一年下來,純收入20萬元穩穩當當。
可是好景不長。2014年,玉米收購價格由原來的1.2元/斤暴跌至0.8元。2014年底,我去拜訪劉能,看到他依舊從容淡定。
“不要怕,農產品市場化,價格起起落落很正常,將來總會漲起來的,這是市場規律。”
“就是玉米八毛錢,也比坐下強!”他的樂觀豁達深深地鼓舞了我。
一直到2020年,也沒有等來預期中的玉米價格顯著回升。然而,新的挑戰卻不期而至:糧價暴跌,地租卻逆勢暴漲!這讓劉能始料不及,家庭農場雪上加霜。
2015年,從市里來了一家牧業公司,流轉土地種植牧草,把耕地流轉費用頂到了500元每畝。
2016年,又從北京來了一個老板,流轉土地種植中藥材,把耕地流轉費用進一步頂到了600元每畝。
我完全能夠想象得到劉能的艱難,但是卻不知道該如何去幫助他。一種難以名狀的情感,讓我甚至沒有勇氣去拜訪他,只能經常向村支書了解劉能的農場經營近況。村支書告訴我,劉能的種植面積在逐年減少,經營的地塊也難以集中連片了,近兩年農場的雇人工錢還沒有給利落。他給劉能算了一筆賬:如果600元每畝流轉耕地種玉米,雇過人工來,種一畝賠200元還得保證風調雨順!
2020年正月初三,我去村里部署新冠肺炎防疫工作,在村口的值班卡點碰到了劉能。看到他身穿一件皺巴巴的人造革皮夾克,頭發稀疏,謝頂嚴重,雖然戴著口罩,但是仍然能看到臉上胡子拉碴。我心里一陣酸楚。
兩個人握了一下手,禮儀性笑了笑,笑得都很勉強。沉默良久,他抽出一支大豐收牌香煙,在我的面前比劃了一下,又立即收了回去。“煙太賴,不能給你抽!”他自顧自把煙點上,猛吸一口,嗆得咳嗽了兩聲。
我問他今年打算種多少畝地,他沒有正面回答,把抽到半截的香煙擲到地上,又把腳踩上去,狠狠地來回搓了幾下,“狗日的種糧大戶!”
接下來,他又恢復了往日的幽默。
“任鄉長,不,現在該改口叫任書記了……你說我是不是窮人?”
我知道他在打趣,沒有回答。
“因為你給報了個家庭農場,害得我連個貧困戶也評不上!價值20萬元的移民樓飛走了!現在村里那些貧困戶,哪一個頂如我饑荒大!”
我們都笑了,笑得心照不宣,笑得五味雜陳。
劉能的困境,折射出一個嚴重問題,這也可能是當下中國最為沉重的話題:瘋狂的地租正在毀掉中國農業!
二、農地流轉價格上漲的邏輯
地租為什么會無理性上漲呢?主要成因可歸納為5個方面。
1. 企業家的盲目自信:了解農業靠新聞,草率入農
薩繆爾森指出,土地供給數量是固定的,因而地租量完全取決于土地需求者的競爭。所以,一些人把地租上漲歸因于城市資本下鄉投資農業,也不無道理。
然而,在現實中,各地的農業公司,如果踏踏實實經營種植業,很少有賺錢的。抬高劉能土地流轉費用的那兩家公司,一家5年沒有見到過效益,另一家也虧損得一塌糊涂。
一些城市工商企業家,由于在原來的行業面臨發展瓶頸,轉而選擇農業。剛下鄉的時候,一個個雄心萬丈,胸有成竹,談起農業來滔滔不絕,對中央一號文件可倒背如流,分析起行業前景來既有歷史高度,又具全球視野。
一號文件讓這些新生農業企業家熱血沸騰,但是現實世界中的農業卻令其懷疑人生。一年后再見面,一個個明顯話少了很多,性格也變得內向了。三年后,許多老板可能連人影都找不到了,留下一個爛攤子,村民索要拖欠的土地流轉費還得上訪找鄉長。
2. 農地的壟斷性
亞當·斯密認為,地租作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價格是一種壟斷價格。
有人會質疑,十八世紀的歐洲,農地高度集中于大地主,交通不發達,農民對耕地的選擇空間不大,才形成了地租的壟斷價格。而目前的中國,耕地掌握在數億農戶手中,地租價格應該接近于自由競爭,如何能形成壟斷?
以下我做一個簡要答疑。
某農業公司流轉耕地,已經流轉到190畝,再有中間的10畝就能實現200畝集中連片經營了。但是,問題出現了,前190畝每畝500元,最后這10畝,農民每畝要600元,給還是不給?如果不給,前面的努力就付之東流了。也許,就在1公里以外的地方,有300元就能流轉到耕地,但是代替不了這10畝。這最后的10畝地就形成了壟斷生產要素!
第二年,其余190畝也需要支付600元每畝,其他農民會說,一樣等級的耕地,為什么張三的你給600元?
事實上,當你承包下第一塊地后,就陷入了農地的壟斷叢林,因為剩下的每一塊耕地都具有壟斷力量。道理顯而易見,規模化經營必須要求集中連片,每一塊相鄰地都是獨一無二,無法替代的。
3. 農民對地租的心理價位脫離了市場規律
由于農地流轉市場不健全,國家征地補償標準為農戶提供了一個流轉耕地的心理參考價位。全國各地,征地補償低則兩三萬元/畝,高則可達二三十萬元/畝。如果補償20萬元/畝,抵得上種植糧食300年的純收入。所以,有的農民擔心耕地流轉出去后,如果遇到國家征地,可能導致與經營戶之間相互扯皮,而現實中此類糾紛確實屢見不鮮。
還有的農民高度重視農地的社會保障功能,想著把地傳給子女,以備不時之需,產權越明確,反而越不愿流轉出去,寧愿撂荒。
許多地方,如瀘州市、橫縣、江安縣等,紛紛出臺了禁止耕地撂荒的相關政策,充分說明我們已經陷入既存在地租瘋漲、又存在耕地撂荒的雙重困境。
4. 農地流轉協調成本太高
由于農地細碎化程度嚴重,一戶農民擁有20畝承包地,也許會分布于10個地塊。企業如果想集中連片流轉到200畝耕地,可能涉及到幾十戶甚至上百戶農戶,有的在包頭,有的在深圳,協調成本非常高。本來300元的流轉市場價,為了加快流轉進度,不得不提高到500元,還得動用大量的社會關系進行協調。
5. 一些涉農政策,推動了地租上漲
為了引導農業實現適度規模化經營,許多地方出臺了強有力的財政支持政策,如支持現代農業產業園建設,支持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能力建設等。而補貼(獎勵)農業經營主體的錢,多數轉化成為地租。增加財政補貼能夠把地租抬高,但是停止補貼后,地租卻不能同步降下來。
由于地租具有價格粘性,財政補貼又缺乏持久性,這使得多數農業種植企業一旦失去了財政補貼就會立即虧損,無法維繼。有人指責工商資本動機不純,下鄉目的就是為了套取農業補貼,補貼到手后就馬上走人。我認為,多數公司的初心確實是踏踏實實經營農業,只是真的經營不下去了!
過去幾年,為了打贏脫貧攻堅戰,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各地大力推動土地制度改革,釋放農地的金融杠桿潛能,推動農村“資產”向“資金”轉變,促使農地成為可以抵押、轉讓、出租、入股的金融資產。
激活農地的金融功能是一把雙刃劍,在增加了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同時,也提高了地租,從而增加了農業的經營成本。
接下來,我再通過建立一個簡易模型來表述地租上漲的邏輯。
農業公司的地租函數:y=ax+b/c+g。其中,y為農業公司所支付的地租,a為當地農戶間小規模農地流轉的平均地租,x為非農化系數,b為企業家的自信,c為企業家對農業的了解度,g為政府支持。
在經營農業上,農民最理性。農戶之間小規模流轉耕地形成的地租a,最接近理性的市場價格。因為農民家庭經營,勞動力不計入成本,農民種田一年賺了3萬,如果付出同樣的勞動,出去打工也能獲得相近的報酬。也就是說,如果把人工算入經營成本,在地租a下,農業家庭經營利潤已經為0。
在公司規模化經營下,人工報酬需要計入成本,但是由于大型農機具的使用,新耕作技術、新水利設備的利用,在地租a下,企業存在一定的盈利空間,然而隨著地租上漲,耕地非糧化和非農化的風險會同步加大。基于晉西北農村的觀察,我得出如下結論:
當1≤x<2時,企業仍然可能找到種糧盈利點;
當2≤x<3時,企業種植糧食無利可圖,只能選擇露天蔬菜、藥材等非糧作物;
當3≤x<4時,企業種植糧食和露天蔬菜都無利可圖了,只能選擇養殖、經營設施農業或種植花卉苗木了;
當x≥4時,經營農業不可能賺錢,耕地非農化不可避免。
從企業角度考慮,該如何解讀以上模型呢?
如果農戶間小規模農地流轉的平均地租a=200,企業流轉耕地是為了種植玉米,那么,企業盈虧平衡點的地租上限值就是400元。如果政府補貼g=0,而企業給出600元的高地租,那么高出來的200元就是企業家的自信度和對農業了解程度的比值b/c。
三、農地流轉價格過高的消極后果
官方文件往往刻意回避使用“地租”這個提法,但是,從“耕地承包費”,到“農地經營權流轉金”,再到近年來方興未艾的“土地入股保底分紅”,都無法改變其地租的本質。
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都認為地租是利潤的一部分。馬克思指出,地租是土地使用者由于使用土地而繳給土地所有者的超過平均利潤以上的那部分剩余價值。李嘉圖定義,地租是由農業經營者從利潤中扣除并付給土地所有者的部分。
而我們許多地方,目前的地租已經顯著超過了種糧利潤,并且仍在以令人不可思議的速度上漲。
地租瘋狂上漲必然導致以下三大消極后果。
首先,挫傷了農業經營者的積極性。全國戶均二畝三分田,專業農民都或多或少需要從其他村民手里流轉耕地。如果地租超過了農業利潤,種田賠錢,不如外出打工。
第二、耕地非糧化。以晉西北為例,如果地租超過300元每年每畝,種玉米難以回本,如果不改變農業用途,只能種植蔬菜或經濟作物。
第三、耕地非農化。還是以晉西北為例,如果地租超過800元每年每畝,基本上都在打非農化的算盤:占地開礦,開發房地產,辦儲煤場,開馬路飯店等。
地租瘋狂上漲絕不是個別地方才有的問題。從甘肅到江西,從黑龍江到云南,和許多鄉鎮黨委書記、鄉鎮長交流,各地普通存在地租不合理上漲的情況。近期,和四川省西充縣農業公司經理趙天潤、湖南農民謝光明等同志交流后,讓我進一步認識到,瘋狂的地租正在毀掉中國農業,危及國家糧食安全。
四、關于農地問題的三個討論主題
農業廢則百業廢。我們應該深入思考,開放式討論,就以下主題凝聚共識。
討論主題1:農地流轉價格是不是越高越好?
提高工商業用地成本,會削弱實體經濟競爭力,讓整個國民經濟脫實向虛。同理,提高農業用地成本,必然會增加農地的非糧化甚至非農化風險,事關國家糧食安全。
然而,每一個個體的理性,并不必然導致群體理性。如果讓全民表決,也許多數人會支持提高地租。
首先,9億農民支持提高地租。雖然半數以上農民已經脫離農業,但是把農村的二畝三分地流轉出去,如果每畝流轉費100元,僅僅收入230元,如果提高到1000元每畝,就可收入2300元,這個賬很好算。
其次,各級干部支持提高地租。提高農地流轉金,農戶的收支測算就能上去,脫貧攻堅工作也就順利完成了。
第三,多數“三農”學者支持提高地租。支持通過盤活土地資產來提高農民收入的觀點,既可獲得高層的支持,又能得到大多數民眾的擁護。而反對提高地租,無異于反對增加農民收入,就可能犯下政治方向性錯誤。
看新聞,某縣某鄉,通過耕地流轉,農民每畝地實現增收1000元,大家一定感到報道充滿正能量。
可是,您有沒有思考過,農民增收的這1000元來源于哪里?
農業企業,也可能是種糧大戶和家庭農場。但是,如果種糧賺不下1000元利潤來支付地租,企業要么破產,要么就只能非糧化或轉行非農產業。
地租價格和糧食種植面積間在玩一場蹺蹺板游戲,此高彼必降。
廣西恭城縣,2010年全縣糧食種植面積26.48萬畝,2019年下降到了4.33萬畝。在全國范圍,又是否存在著嚴重的耕地非糧化問題?我們是否已經做好了風險應對準備?
上世紀90年代,農民負擔沉重,農業稅和“三提五統”居高不下,形成了嚴重的“三農”問題。農民負擔沉重的本質是什么?就是地租提高了,農業不賺錢了。
我的觀點: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無論工商業還是農業,炒作土地都是飲鴆止渴。
討論主題2:誰是當代農民?
第一個問題:到農村流轉土地經營農業的城里人,是農民嗎?
許多所謂的工商資本下鄉,規模并不大,老板吃在農村,住在農村,參與農業生產勞動。
老常是一位國企下崗工人,到村里承包經營了200多畝耕地,帶著老婆,住在山溝里的幾間土窯洞里。窯洞以前有人養過羊,條件非常艱苦。
國家出臺了種糧大戶獎勵補貼政策,我給老常也申報了,但是未能審批下來,原因是老常的身份不是農民。
一些同志根深蒂固地認為,工商資本下鄉,就是去壓榨剝削農民的。
我認為,規模大小迷惑了我們對問題本質的判斷。我們應該正視一個現實:是城里人租地,農民出租地,所以農民才是新興地主,而下鄉的城里人應該是當代佃戶才對。只是過去全國僅有數千個大地主,現在變成為數億個小地主,過去100個小佃戶對一個大地主,現在變成為一個大佃戶對100個小地主而已。
那么,究竟是誰在剝削誰?
現實中,投資種植業的城市資本,由于地租太高,多數不是已經破產,就是在破產的路上。農民得了高地租,城里人當了“楊白勞”。
第二個問題:脫離農業、農村的“農民”還是農民嗎?
接下來讓我們分析一下已經離開農村,脫離農業,但是仍然擁有農村戶口,擁有農村宅基地、承包地的這一部分農民,為了和真正務農的農民區分,我將其標識為帶引號的“農民”。
提高地租,對于真農民,可能會降低收入,因為真農民不但自己的耕地不會出租,而且還需要從外面租入耕地。
但是對于進城“農民”而言,地租就是家庭收入的一個重要源泉,他們不依賴農業經營收入,但是渴望盡可能提高耕地流轉費用。所以,進城“農民”是地租上漲的最大動力。
從全國范圍考量,進城“農民”戶均二畝三分地,即使地租每畝每年1000元,也僅能收入2300元。2300元不多,但是從長期來看,足以毀掉中國農業。
地租一旦成為了社會福利,上去容易下來難。目前這種數億小地主局面,可能會給中國農業帶來災難性后果。由于涉及利益群體太過龐大,目前和將來,學者沒有勇氣去質疑高地租的合理性,高層也難下決心去降低農業經營成本。
事實上,進城“農民”享受不到同等的城市子女教育權益,享受不到企業工人的退休待遇。我們沒能保障好進城“農民”應該享有的國民待遇,卻固化了其本該退出的農村權益。而后者,可能既降低了農地利用效率,也違背了“耕者有其田”的社會主義目標,培養出一個龐大的食利群體,拖垮了中國農業,短期內提高了“農民”收入,長期內卻砸掉了子孫的飯碗,給國家治理帶來史無前例的巨大挑戰。
我的觀點:我們應該給予進城“農民”平等的城市居民待遇,同時,也應該賦予下鄉“城里人”平等的農民權益。
討論主題3:解決農地細碎化問題,應該靠市場力量還是行政手段?
有機構統計,全國目前戶均5.58畝耕地,分散為5.08塊!太谷縣任村鄉,累計核查出集體機動地8343.18畝,分布于3600個地塊上,其中面積在1畝以下的耕地973塊。
80年代初期,由于農村勞動力過剩,耕地細碎化不僅不是問題,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就業壓力,維護了社會穩定。
現在情況剛好相反。我曾認真觀察過農民的勞作過程:相鄰地塊間的開畔剎墑,農民從一個地塊到另一個地塊間的勞動轉換,可能會耗費三分之一的有效勞動時間。由于農地細碎化,年輕人覺得經營農業效益太低,不如外出打工,農地細碎化排斥了優質農業勞動力。
耕地細碎化,已經嚴重制約了中國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發展。
如何才能夠實現農地適度規模化經營呢?目前學術界達成了空前的一致:依靠市場力量!
我認為,如果完全依靠市場力量來解決農地細碎化問題,可能需要5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我花費三年時間研究過農民的換地流程,結論很悲觀:即使在一個結構簡單的村莊,一戶農戶如果想把自家分布于10個地塊的20畝耕地并為一個地塊,就會涉及到全村所有農戶。
同時,由于地塊細碎化、農地承包經營權細碎化,城市資本下鄉連片經營農業,流轉耕地的協調成本太高,企業在農地壟斷叢林中步履維艱。
近期,我在思考:學術界是否嚴重低估了我們的制度優勢,把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發展成就,過多地歸因于市場經濟?農業又能否過度市場化?
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農業的補貼力度很大,地租也控制得非常低。各國普遍奉行農業“計劃經濟”道路,為什么卻要把農地生產要素配置“由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理念輸出到中國呢?
家庭聯產承包改革推行初期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否恰好是因為農村計劃經濟沒有充分放開,較好地發揮了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兩方面優勢,找準了二者的最佳平衡點?
我相信,在目前的農業生產力發展水平下,如果從政策層面允許通過行政手段來靈活調整耕地,那么在確保不傷害農民利益的前提下,農地細碎化難題將迎刃而解……
我的觀點:大道至簡,學術研究應該回歸常理思維。農地政策必須基于田野調研,而不僅是科斯定理。如何避免陷入高深理論偽裝下的低級陷阱,可能是21世紀中國“三農”研究的最重大課題。
作者:任盛宇(山西農谷鄉村調查研究院)
 網站導航∨
網站導航∨